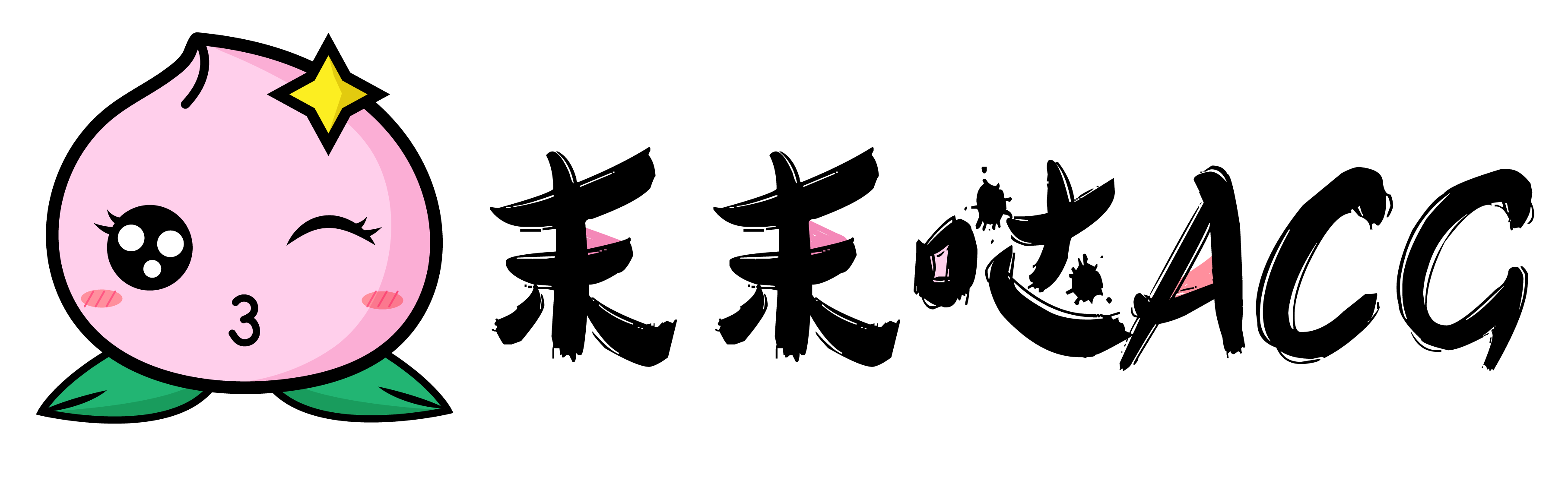- A+
国内可能再没有哪本杂志像《儿童文学》这样,对不同年代的订阅者来说,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读者来说,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儿童刊物,也是新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摇篮;对于八九十年代的读者来说,它是一本“名不符实”、内容相当深刻的文学杂志,是当时的纯文学重镇;而对于21世纪的新时代读者来说,它就是一本再平常不过的少儿纸质刊物。
这可能是因为,作为一本历史悠久的名刊物,《儿童文学》却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办刊理念。这其中有偶然,也有历史的因素。
对这份刊物而言,可能只有摸起来粗糙不平的蜡制封面是唯一不变的东西。
1
《儿童文学》创刊于1963年。虽然刊名如此正式,但创刊后的十几年里,它连刊号都没有,算是一本“内部刊物”。
1963年,正值三年自然灾害(或称“三年困难时期”)刚刚结束。物质生活的匮乏影响到了精神领域,给成年人看的报刊杂志也不算多,何况是儿童读物。当时全国只有2家专门出版童书的出版社,有影响力的刊物几乎只有上海的《少年文艺》一本。
《少年文艺》创刊更早,但是由于位处上海,很难征集到北方作家的稿件。
为了解决这种情况,由叶圣陶、茅盾、冰心、金近等一批作家和画家倡导,在北京创办了《儿童文学》。
第一期《儿童文学》的编委,叶圣陶居首
著名儿童文学家,也是创刊人的金近在创刊词中写道:“回首四顾,这里还是留下了一大片未经开拓的荒原,有待耕耘。即以成长起来的花木来看,也还是品种不繁,干株不坚,既无参天古木,也少奇花异草”,算是对当时儿童读物状况的概括。
最初的《儿童文学》没有刊号,也没有固定的发行周期,编者只能表示“大概每年出四期”。与其说是一本杂志,倒更像是一批儿童文学作品的汇编集。
但它汇编的作品阵容却非常豪华:叶圣陶、金波、冰心等知名作家的文章频频出现;杂志的理念也很现代:几乎每篇文章都配有专门绘制的插图,插图的水平大都不低,比如创刊号的封面图就是黄永玉的木刻作品,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
黄永玉的木刻封面图
同类刊物少,质量又优秀,《儿童文学》顺理成章地大受欢迎,第一期就卖出了30多万册。编者们也对杂志的前景很有信心,准备将杂志发展成全国发行的“外部刊物”,发行周期也固定下来。创刊的第二年,编辑部还把全国的青年儿童作家请到北京举办学习会。
这种信心没能持续太久。《儿童文学》创刊的1963年,离十年文革的开始,只差3年。
文革期间,《儿童文学》先是大幅增加了革命主题的作品。但是这种作品儿童并不爱看,再加上很快文艺界的情势恶化,《儿童文学》在出版了10期后宣布停刊,一停就是十年。
直到1977年,一篇名为《“四人帮”是摧残儿童文学的刽子手》的文章,才宣告了《儿童文学》的重新出版。十年前就开始谋划的“固定出版周期、面向全国发行”又被耽搁了好一阵子。
然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,《儿童文学》都只是一本普通的儿童杂志,读者群体局限在小学生群体中。
它真正变得“名不符实”,不再局限于“儿童”这一群体,而是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中奠定了地位,还是因为90年代的文学杂志大危机。
2
上世纪80年代,中国的文学创作迎来了一次反弹式的爆发。北岛、舒婷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,满大街都是诗人,满大街都是文学杂志。
儿童读物也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增长。几乎每个省都办了自己的儿童刊物,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的发行量也破了50万。
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久。
北岛回忆说:“那是由于时间差——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。没两天,商业化浪潮一来,这种狂热就不复存在了”。
到了90年代,文学热迅速退潮。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大幅下滑,儿童刊物也被波及,到1996年时,《儿童文学》编辑部做了调查,发现各省的纯文学刊物几乎都没了,“八十年代一哄而上,现在好像是秋风过境,一夜之间都消停了”。
《朝花》、《未来》等大型儿童期刊相继停刊,《儿童文学》自己也岌岌可危,发行量一度只有6万册。
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彻底转型。虽然靠文学卖不出了,但儿童刊物还是有很大市场空间的——做教辅、做作文选,甚至是直接转型成综合性杂志,都能保证杂志卖得出去。
如果《儿童文学》选择了其中任何一条路,也就没有了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,“完全不儿童”的《儿童文学》了。
1991年起出任杂志主编至今的作家徐德霞在多年后回忆说,那时候国内只剩下十几家儿童文学类刊物,有一些开始专发学生的作品,认为这样可以吸引小读者,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:不仅继续搞文学,还要搞最纯的纯文学,不搞通俗文学,不搞“故事”,而是要把要把全国艺术品质最高的作品拉到《儿童文学》里来。
1997年,《儿童文学》在杂志封底印上了“本刊适合9至99岁公民阅读”的字样。
这行字奠定了之后十几年《儿童文学》的基调,把它变成了各种文学内容和题材的试验场,和无数青少年纯文学的启蒙杂志。
《儿童文学》那时登载过什么样的作品呢?
有《跑,拼命跑》这种反思高考和过激的应试教育体制的作品,讲述了高考前老师和同学的一系列变化。文章最后,主角的一位朋友被切换户籍来获得高考加分的同学刺激,进了精神病院,却在高考当天逃出来想闯进考场。
2011年贴吧对这篇作品的回忆
类似的作品还有《青春流星》,讲了一位被家长老师寄予厚望的高中女生,因为压力过大在奥数比赛上作弊,被抓了。结局是这位女生选择了自杀。
还有饶雪漫的《谁可以给谁幸福》,情节是一位16岁少女因为被抢劫重逢了童年好友,因此产生了一段纠葛的关系,给了很多当时还完全不知道“青春伤痕文学”为何物的读者很大震撼。
《儿童文学》设过一个科幻栏目。刘慈欣在上面登载过《圆圆的肥皂泡》一文,故事主体是利用无数大肥皂泡裹带湿润空气进入内陆,从而调节气候。当时刘慈欣的笔法和风格已经有了后来《三体》、《流浪地球》的影子。
这种对虚构宏大事物的描写一直贯穿刘慈欣的作品之中
2005年后,在电子游戏还被污名化为“电子海洛因”的时候,《儿童文学》就登载了不止一篇网游小说,主题大多是玩家打破了第四面墙。有《亡灵骑士录》,讲了一群玩家集体变成了Boss,结尾有“从不接触网络游戏的人,知道有那样一个世界吗?”这样的句子。
还有《圣域传说》,内容是一名玩家在游戏中带领NPC利用Bug毁掉了游戏,最后发现他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也是别人设计出来的游戏。
前者取材自《魔兽世界》,后者的背景是《仙境传说》。
当年NGA对于《亡灵骑士录》一文的讨论
如果说上面的作品还大多以校园为题材,那余华的《我胆小如鼠》一文就彻底离开了校园。这篇小说的很大篇幅都是讲述勤奋、诚实却胆小的主角工作后被同事欺压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描写了“一个畸形的社会,一种不健全的社会,一种不成其为社会的社会”。
很多在《儿童文学》上登载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改编成了长篇作品。比如上面提到的《谁可以给谁幸福》,改编为了长篇青春小说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;《圣域传说》改编为了“校园幻想作品”《圣域的传说》。
一般来说,我们把年龄小于14周岁的孩子叫做儿童。然而这个时期《儿童文学》上的大部分作品,没到14岁是没法完全理解其中深意的,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看了之后就一无所获。大部分当年的《儿童文学》读者都提到一个说法:“虽然当时有些看不懂,但是后来再读觉得回味无穷”。
很多人即使到了完全称不上“儿童”的年纪,也还在订阅《儿童文学》。《纯真年华》的作者安武林就提到了他上大学时还自己订阅了《儿童文学》,让一些同学很是惊讶。
《儿童文学》成了一整个年代的人对于文学启蒙的共同回忆。
2016年一条关于《儿童文学》的微博有1万多转发,3000多评论
3
这些都已经是辉煌的过去,现在的《儿童文学》已经不再是这样。
2009年,有人在豆瓣指责《儿童文学》越来越低龄化。底下也有些人回应说,小时候觉得很好看,后来又买了一本,发现“已经纯粹是给小孩子看的了”。这个帖子2016年还有人评论“原来五年前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”,之后就再也没有跟帖。
这其实是个很奇怪的说法。不管是《儿童文学》创刊的宗旨,还是它刊名的含义,都表明了这本来就是一个给低龄儿童看的杂志。2010年后的《儿童文学》确实也逐渐放弃了曾经的纯文学立场,开始回归通俗故事和动物拟人。
2019年《儿童文学》里的一篇文章,主题和写法明显都比当年低龄化了很多
但如果考虑到这本杂志当年给那么多人带来的震撼,这种指责也就算不上奇怪了。
2014年,《儿童文学》改版,分为了“少年”和“童年”两个系列,每个系列下设两个分刊。经典版登载诗歌、小说和散文等原创作品,选萃版回顾已经发表过的文章,美绘版以图片为主,而时尚版,则和主编徐德霞当年引为反面例子的某些杂志一样,主要接受学生投稿,这个时尚版很快也被取消,改为了故事版。
分刊之后的《儿童文学》
这种对读者的分层首先就让“适合9到99岁阅读”的承诺不再那么有说服力。另外,即使是属于少年系列的经典版和选萃版,其中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也都比从前差了不少,很多时候需要靠翻译的国外作品填充版面,像过去那样百花齐放的局面,是再也没有了。
2019年9月选萃版的科幻栏目,除了导读,全是国外作家的作品
这也没什么大不了,一本杂志有自己的生命阶段,就和它的读者一样。如果你是一个当年喜欢过《儿童文学》、希望它永远像当年那样的读者,不妨回到最初,看看1963年10月,《儿童文学》创刊号第一篇文章里的第一句话:
谁没有自己的愿望?愿望是生命的食粮,它跟随我们的年龄一起成长。
来源:游研社